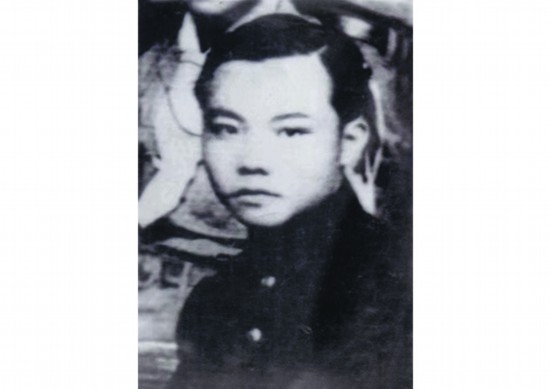
許運伙
1929年春天,春風和煦,萬物復蘇。深滬灣內風平浪靜,舟楫零星,一艘漁船緩緩駛向更廣闊的海域,船上站著個穿著粗灰布衫的年輕人,眼睛直勾勾地望著這片正動蕩迷茫的土地,船越來越遠,越來越小。一個來自深滬漁村的普通小伙子要下南洋,投奔伯父,求學就業。
他叫許運伙,1912年出生,祖籍福建晉江深滬呂宅村。許運伙出生后不久便遭命運的暴擊,父母因貧染病,相繼過世,他成了孤兒。幼時的苦難磨礪他生命堅毅頑強的底色,成年后如碑一樣堅固的革命信仰,也是來自這份淬煉。后來,許運伙投靠伯父許景送,決心下南洋求學問、謀人生。
堂親伯父把他當自己孩子看待,就學於南洋宿務市中華中學的許運伙,很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機會,決心發奮學習,刻苦鑽研,處處爭當學校的先進分子,常常以優異的成績回報恩同再造的伯父及告慰父母的在天之靈,性格又低調謙和,總能和同學們友好相處,在同學中有一定的威望。許運伙成了校長劉春澤重點關注對象,劉春澤是旅菲華僑的進步人士,經常向學生傳播進步思想和馬克思理論,宣講革命理想和道義。許運伙在校長的耳濡目染下,革命火種至此在心中萌芽,並迅速茁壯,成為一名有信仰勇追求敢擔當的優秀青年。
許運伙深知,要追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運動,就必須回國,回到跌宕迷茫的故土,因為那裡才是熱血呼應的地方。1936年,他秘密回國,很快被發展成為一名地下革命青年,並結識了進步人士何必然。抗戰爆發后,他們倆從上海偷偷返回晉江,認識了朱漢膺、李剛,得到上級的指示,潛入石獅的坑東小學任教,以教員身份做掩護,開展地下革命活動。不久,許運伙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以黨員身份活躍在深滬、東石、英林沿海一帶,開展抗日救國運動,革命宣傳活動,培養進步青年,創建交通聯絡站。后來,他輾轉來到東石塔頭村的中山學校,頻頻往返塔頭黨支部,這是許運伙革命生涯無法繞過的地方,也是他短暫的生命裡最為絢爛的篇章之一。

塔頭劉村劉氏祠堂
許運伙經常活動在沿海區域,塔頭村是他頻繁來往的地方,他在中山學校裡,白天以教員的身份講政治理想,授文化知識,晚上則注重發展革命力量,培養革命人才,經常深入到群眾中間發表演說,有的是在民宅裡義憤填膺,有的會在農田裡大聲疾呼,揭露日寇侵華暴行,控訴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講述國民黨反動派剿共罪行。許運伙經常借著月光,講到深夜,大家也樂此不疲。1938年到1939年間,他與朱漢膺、李剛先后介紹劉偶才、劉乾隆、劉廷都、劉基固等青年才俊加入黨組織,發展一批又一批的進步青年,壯大革命力量。1940年,他又介紹了更為年輕的劉廷如加入組織,並委派他到深滬呂宅村(許運伙的家鄉)任支部書記。這些青年,紛紛成了塔頭中山學校地下交通聯絡站的革命骨干,成了塔頭地下黨組織的核心人物,在閩南沿海革命的歷史長卷裡,他們的革命事跡可歌可泣,他們的音容笑貌,天地不朽。特別是劉廷都、劉長來、劉國良等青年志士,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即使身陷險境,仍能祭出堪比青天的氣節,慷慨就義,給予后世垂范千古。
追憶許運伙在塔頭的事跡,除了在培養革命優秀青年上的一片赤誠,他在泉州參與策劃的一起“搶米斗爭”不可不說。
1940年4月,時令不濟,農民欠收,經濟狀況每況愈下,投機倒把者趁火打劫,群眾的生活更加艱難,一些奸商經營的糧店,開始囤積居奇,哄抬米價,倒行逆施,當時反動政府卻不聞不問,坐看經濟規律失衡,民不聊生。中共泉州中心縣委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決定在泉州地面上發動“搶米斗爭”,目標直指反動政府和巨賈奸商的糧倉,以疏解民生疾苦。當時,任中共泉州中心縣委委員的許運伙率領游擊隊參加針對美耕米店的斗爭,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搶米斗爭”,中共塔頭地下支部和人民群眾也積極響應和參加,完成了重要的任務。在李剛、許運伙的指揮下,高呼“打倒奸商”等口號,沖進美耕米店,把幾十包大米抬到街上分給群眾。這場斗爭擴大了中共的政治影響力,也引起反動派的瘋狂反扑。中共泉州中心縣委書記曾白羽被捕叛變,黨員蘇棠影、張劍華、呂少華等先后被捕。身處險境的許運伙,挺身而出,重新恢復黨組織。同年9月,許運伙被任命為中共泉州中心縣委書記。他身負重任,奔波於晉、南、惠等地,努力恢復和發展基層組織,為籌建抗日游擊隊做好准備工作。

廷都中心小學新貌
對許運伙而言,塔頭劉村、塔頭中山學校地下交通站(今改名“廷都中心小學”)、劉廷都、劉乾隆以及那一張張可親可敬群眾的臉龐,必定是他生命裡無法拂去的記憶。對塔頭劉村來說,那一段段熱血與烽火交加的革命歲月裡,許運伙是豎在人民群眾心頭上的一座不朽的碑。革命的美好,是志同道合者的相遇。在這裡,塔頭劉村與許運伙相遇了。
1941年10月31日,許運伙召集侯如海、施贛生等到家鄉呂宅村工作。中午時分,當他們准備休息時突遭國民黨警察,為掩護其他同志以及秘密文件,許運伙與國民黨警察展開槍戰,終因寡不敵眾,在搏斗中,胃部中槍血流不止,壯烈犧牲,年僅29歲。一位才華橫溢的黨的好兒女從此隕落,山河含悲。
1947年11月,中共閩中地委把原沿海區命名為“運伙區”。新中國成立后,晉江縣人民政府正式把許運伙出生的村落改名“運伙村”,並建造起一座許運伙紀念亭。關於銘記,沒有比名字嵌入故土更好地表達了。
烈士已成精神的豐碑,故事已換嶄新的容顏,那些以烈士命名的道路、村落以及公園,他們乘載的不僅僅是記錄一份榮光壯闊的記憶,更是一種精神的指向和奮斗志向。隻有人生價值觀的確立,才知道我們從何而來,應該向何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