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成為歷史的主流,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以《新青年》創刊,陳獨秀高舉“文學革命軍”的旗幟為標志,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中的一批先進分子,在那個落后、貧窮、黑暗且任帝國主義宰割蹂躪的時代,開始以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為己任,重新考慮中國的前途命運,探求改造中國社會的新方案。他們紛紛創辦刊物、成立社團、撰寫文章,研究、介紹和傳播國外的各種思潮。1919年,據不完全統計,僅北京一地登記在冊的社團就有281個,全國各地創辦的期刊達600多種。
1918年7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上發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公開說明自己為什麼要“談政治”。他說:“本志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養學識,從根本上改造社會,何必談甚麼政治呢?有人說:本志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議時政,現在何必談甚麼政治惹出事來呢?呀呀!這些話卻都說錯了。我以為談政治的人當分為三種:一種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職業﹔他所談的多半是政治中瑣碎行政問題,與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不同。一種是官場以外他種職業的人,凡是有參政權的國民,一切政治問題,行政問題,都應該談談。一種是修學時代之青年,行政問題,本可以不去理會﹔至於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作啞呢?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系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國人其速醒!”

李大釗

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
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一下子擊碎了人們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幻想。五四運動的爆發,促使中國思想界相當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義的同時,也開始懷疑以至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轉而向往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現時和將來的人類共同的思想”。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誠如瞿秋白所說:“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
新思潮來勢洶涌,好像“洪水猛獸”,沖破了傳統思想的禁錮,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大解放。波濤滾滾,泥沙俱下。即使是他們當中的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一開始也還只是一種朦朧的向往,猶如“隔著紗窗看曉霧”,無法分清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一時間,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泛勞動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伯恩斯坦主義,等等,雨后春筍,紛然雜陳。當年就有人評論說:“譬如社會主義,近來似覺成了一種口頭禪﹔雜志報章,鼓吹不遺余力﹔最近,則與社會主義素來不相干的人也到處以社會主義相標榜。”
1919年底,工讀互助主義實驗活動在北京、天津、上海、長沙、南京、武漢、廣州等地的進步青年中興起。他們組織互助一類小團體,在“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照耀下,過起了“共產的生活”,希望把這種工讀互助團逐漸推廣到全社會,從而實現“平和的經濟革命”。與此同時,還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國的勞動共產村的做法,在中國進行“新村”試驗。
然而,在現實面前,這些中國“新村”也是曇花一現。試驗的失敗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青年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社會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試驗新生活”﹔“要改造社會,須從根本上謀全體的改造,枝枝節節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的確,在那個歷史現場,許多人最初對社會主義的討論,有無限的興味,但大多數只是抱著一種空泛的理想,認為必須改造現有這個惡濁的社會,建立起一個新社會來。但是,舊社會如何改造?新社會如何建立?新社會應該是什麼樣子?這一切都沒有現成的答案。劉仁靜回憶說:“那時,大家正在尋找國家的出路,追求真理,對社會主義還沒有明確的認識。研究會的幾十個會員中,除部分相信馬克思主義以外,有的相信基爾特社會主義,有的相信無政府主義。其實,在當時他們對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也沒有什麼研究,只是從雜志上看了一些有關宣傳品,認為有道理,合乎自己的胃口,以后看見別的主張更好,有的也就放棄了自己原先的主張。”
誰的青春不迷茫?救亡圖存,愛國救國,有志青年也有茫然的時候,一時間失去了方向感。彼時的中國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彼時的青年也站在十字路口。
當然,那時候的中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確實很少很少。最早零星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論到中國的,是清末民初的外國傳教士、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1920年以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中文全譯本一本也沒有,列寧的文章還沒有一篇被譯成中文。在這種情況下,談馬克思主義,困難可想而知。李達回憶說:“當時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過來,我們只是從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得自日本的幫助很大,這是因為中國沒人翻譯,資產階級學者根本不翻譯,而我們的人又都翻譯不了。”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這時,站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釗。
1889年10月出生於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的李大釗,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李大釗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受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的影響,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后,他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在《青春》一文中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的同學、后來同在《新青年》擔任編輯的高一涵說:“他在日本時學的是經濟學,但他對那時資本主義經濟學總是不感興趣,一看到河上肇博士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論著,就手不釋卷。他從 1917 年俄國二月革命起,經過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1918年至1922年間,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的工作室
橢圓的臉,細細的眼睛,長長的八字胡子,藍布袍,黑馬褂,一副金絲圓框眼鏡,這是李大釗留給人們的典型印象。作為北京大學新任圖書館主任、教授,李大釗的月薪在1918年的時候是120元。但他把三分之二的薪水用在公共事業上,剩下三分之一的家庭生活費還拿出來接濟貧困學生。夫人趙紉蘭經常因生活費不夠而發愁。校長蔡元培得知后,曾關照會計科說:“每月發薪時要先扣除李先生一部分,親手交給李夫人,免得她‘難為無米之炊’。”每天清晨上班,從西城到東城,李大釗都堅持步行,不乘人力車。午飯是一張大餅,或兩個饅頭,就白開水下肚。人們把他的生活歸納成十六個字:“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陳獨秀評價李大釗說:“他對同志的真誠,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臘月,將自己新制的棉襖送給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他都熱情地招待飲食)沒有餓著肚子走出來的。”北京朝陽大學學生張爾岩回憶,他曾勸李先生要注意營養,保重身體。李大釗回答他說:“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嘗不企享用?但時下國難當頭,眾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面對這種情況,我怎忍隻圖個人享受,不思勞苦大眾疾苦呢?”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李大釗告誡青年學子:“青年之文明,奮斗之文明也,與境遇奮斗,與時代奮斗,與經驗奮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華也。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
1919年9月,在李大釗的主持下,《新青年》推出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同期,發表了李大釗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介紹。他寫道:“自俄國革命以來,‘馬克思主義’幾有風靡世界的勢子,德奧匈諸國的社會革命相繼而起,也都是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馬氏社會主義的理論,可大別為三部:一為關於過去的理論,就是他的歷史論,也稱社會組織進化論﹔二為關於現在的理論,就是他的經濟論,也稱資本主義的經濟論﹔三為關於將來的理論,就是他的政策論,也稱社會主義運動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即階級斗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所以他的唯物史觀說:‘既往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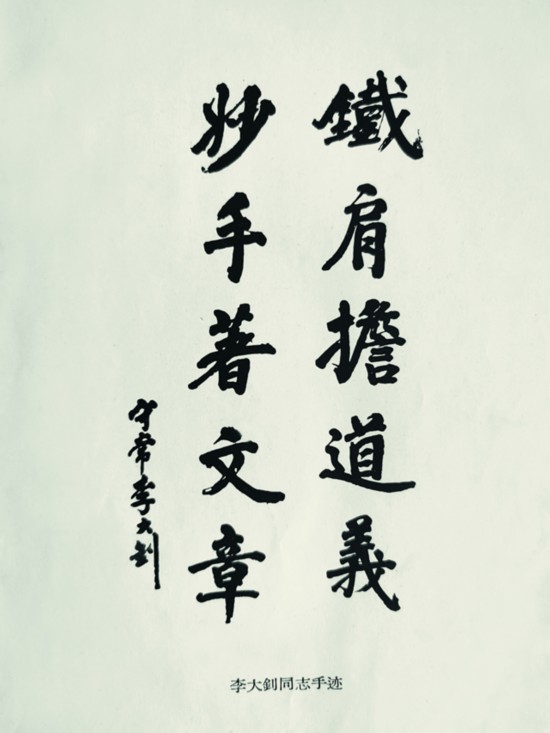
李大釗手跡: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於真理。”這是李大釗的座右銘。
和以往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所作的片斷的、不確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闡釋已經相當完整和確切。盡管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先驅河上肇教授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一書中材料所寫,但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更顯難得而可貴。此前,還幫助自己曾經就職的《晨報》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以連載形式編輯發表過淵泉(陳縛賢)譯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斗生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馬氏資本論釋義》等文章,前兩種也譯自河上肇的論著。這個時候,李大釗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迅速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此,他開始了“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實踐。
像李大釗一樣,青年學子楊匏安和李達,因在留學日本期間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學說,回國后也翻譯、傳播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11月至12月,楊匏安在廣東《中華新報》上發表了長篇連載文章《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作了相當系統的介紹。1919 年,李達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先后發表《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不同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不同的”。緊接著,他又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三部著作,寄回國內出版。留學美國的張聞天也發表了《社會問題》,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每周評論》《民國日報》《建設》等一批報刊紛紛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達200多篇,其中很多是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譯文。1919年4月6日的《每周評論》在摘譯《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內容時,編者還加了這樣一段按語:“這個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見。他們發表的時候,是由1847年的11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張階級戰爭,要求各地勞工的聯合,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北方和南方各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
在北京,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紅樓發起建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正式公開成立。當時因躲避北洋政府當局的搜查,初名為“馬爾柯斯學說研究會”。李大釗還別具匠心地將研究會集體學習的圖書館取名“亢慕義齋”(英文Communism 的音譯,又叫“康慕尼”,意為“共產主義”)。“亢慕義齋”是中國第一個馬列書刊的翻譯室,下設英文、德文、法文三個翻譯組。發起成立這個研究會的成員主要有高崇煥、王有德、鄧仲澥、羅章龍、吳汝明、黃紹谷、王復生、黃日葵、李駿、楊人杞、李梅羹、吳容滄、劉仁靜、范鴻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宏、朱務善、范齊韓等。預科德語班學生羅章龍最早翻譯了德文版《共產黨宣言》,並出版油印本。毛澤東 1920 年到北京時曾經閱讀過。
為了找到房子,羅章龍專門去找校長蔡元培。沒想到,蔡校長非常痛快,立即答應,在北大西齋離校長室不遠的地方給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兩間房子,一間做圖書館,一間當辦公室。當時,也有人反對把房子給“激進分子”,蔡元培說:“給他們房子,把他們安置好,學校才會太平。”分得房子,大家歡天喜地,連日聚會。一位名叫宋天放的會員手書了一副莫名其妙的對聯:“出實驗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上聯出自陳獨秀五四運動時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隨感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下聯則出自李大釗的手筆。今天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還收藏有“亢慕尼齋”印戳的圖書。
人間芳菲四月天。北京的四月天,春風送暖,柳樹兒也才冒出嫩綠的鵝黃芽葉兒。
1920年4月的一天,王府井大街的外國公寓來了五位客人,聲稱是俄文《生活報》的記者團,准備來北京籌辦一家“華俄通信社”。帶隊的這位風度翩翩、文質彬彬、中等身材的青年人,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名叫格列高裡·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時年27歲。與他隨行的有旅俄華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員、翻譯楊明齋,兩名助手季托夫和謝列布裡亞科夫(朝鮮人金萬謙),以及他的夫人庫茲涅佐娃。
出身貧寒的維經斯基,小學畢業后當過排字工人,做過會計,20歲的時候離鄉背井遠渡重洋到美國謀生。在美國,他參加了社會主義政黨,開始從事政治活動。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后,他返回俄國。1918 年,他在海參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了俄國共產黨。1919 年遭到逮捕,被判處無期徒刑,流放到薩哈林島(庫頁島)服苦役。后來,他憑著出色的組織才能,領導政治犯成功地舉行了暴動,一舉成名。1920年4月,受外交人民委員會遠東事務全權代表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的派遣,在俄共(布)西北利亞局遠東州委海參崴分局負責遠東事務的維經斯基來到中國,了解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情況。到中國后,維經斯基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叫吳廷康。1920年9月,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成立,維經斯基是書記處委員,開始以全權代表身份在中國工作。
作為翻譯的楊明齋,原名楊好德,山東平度人,人生也不平凡。1901年,19歲的他“闖關東”“下崴子”,靠當苦工兼記賬員度日,學會了俄語。1908年,在西伯利亞當礦工時,楊明齋參加了俄共(布),並在十月革命后被保送入莫斯科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馬列主義。畢業后,他受派返回海參崴,以“華僑聯合會負責人”身份做地下工作。這次作為維經斯基使華小組的重要成員,發揮翻譯、參謀和向導的作用。后來李大釗稱贊他是“萬裡投荒,一身是膽”。
第一次來中國,人生地不熟,維經斯基還是先找俄羅斯老鄉熟悉情況。在北京大學,他見到了被譽為“中國通”的漢學家、俄籍教授波列伏依,他的中文名字叫柏烈偉,也叫鮑立維。柏烈偉傾向革命,與俄共(布)的許多人士保持友誼,在北京、天津、上海結交了許多進步文化人士。陳獨秀、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新文化運動報刊,他也是熱心讀者。就這樣,柏烈偉給維經斯基推薦了陳獨秀、李大釗。因為陳獨秀已經離京,維經斯基就和李大釗見面了。這一年,李大釗31歲,比維經斯基大4歲。
1920年,因為蘇俄政府發表對華宣言,廢除沙俄政府時期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蘇聯人的好感油然而生。當維經斯基提議召開一個進步人士的座談會時,李大釗一呼百應,門庭若市,一些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積極報名參加,主要成員是張國燾、羅章龍、李梅羹、劉仁靜。
第一次見面座談是在北京大學紅樓的圖書館舉行的。座談會一開始,維經斯基給大家分發他帶來的《國際》《震撼世界的十日》等宣傳十月革命的書刊。這些書刊,既有俄文版、英文版,也有德文版。接著,他向大家介紹了十月革命的經過和意義,講解了蘇俄的各項政策、法令,還講到了俄國當前面臨的種種困難,以及為了克服困難而採取的措施,比如,不得不臨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余糧征集制度等等。
維經斯基說:“中俄兩國的國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帝俄時代的俄國經濟比西歐落后 50 年到 100年,工業生產尤為落后,汽車、拖拉機、飛機、電氣設備都不能制造。鋼鐵工業的產量比美國少7倍,比德國少3倍﹔燃料比美國少17倍,比英國少10倍。外國資本佔全俄一半,外資工業佔5%,外國銀行佔全俄金融資本 。當前追趕上去的唯一辦法,就是採用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正在開辟一條新的道路。”
有理有據的分析,合情合理的介紹,讓羅章龍、張國燾等年輕人大開眼界,他們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對蘇維埃制度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看到了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輪廓。
維經斯基英文和德文的水平都很高,可以用英語直接對話。座談會上,他在回答了中國朋友們的提問之后,還有針對性地詢問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頗有研究,對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相互勾結的情況也看得十分清楚,對五四運動的情況問得非常仔細。
通過集體的座談交流,能言善辯、目光深邃的維經斯基一下子征服了中國年輕的學子。年輕學子們感覺他是一個具有煽動力的人,思想感情奔放,說辭新穎動人,對十月革命、對蘇維埃制度也更加有信心了。
交談中,維經斯基帶有暗示意味地說:“在座的同學們都參加了五四運動,又在研究馬克思學說,你們都是當前中國革命需要的人才。你們都應該好好學習,要了解十月革命,中國也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
會上會下,維經斯基與李大釗談得十分融洽,相互間的印象很好。根據蘇俄革命經驗和了解到的中國實際,維經斯基對李大釗說:“中國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接著,他進一步分析說:“北京是軍閥統治的中心,又沒有什麼工業,工人階級的數量太小﹔廣州的工業也不發達,又是各派斗爭的焦點,太引人注目。隻有上海,既是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無產階級眾多、集中,又是先進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在那裡建立黨團組織的中心,比較適宜。”
李大釗對維經斯基的觀點深表贊同,並建議他盡快去上海找陳獨秀商議,因為在這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的旗幟、新思想的明星,沒有人能夠比他更有影響力、凝聚力和號召力。
在上海,1920年5月,陳獨秀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主要成員有李達、李漢俊、沈玄廬、沈雁冰、施存統、陳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馬克思主義傳播就這樣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南方由陳獨秀負責,北方由李大釗負責,時稱“南陳北李”。就這樣,以北京、上海為中心,他們先后與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的日本、法國一批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了聯系,輻射並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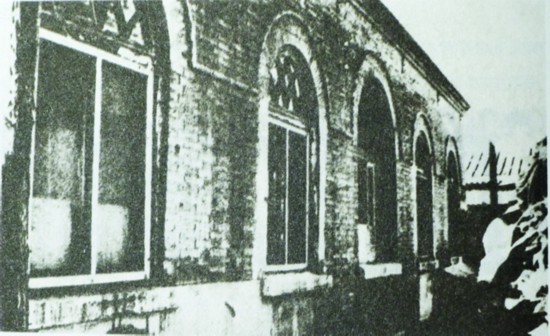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大紅樓發起建立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1年11月17日,公開正式成立。圖為該會活動場所“亢慕義齋”舊址
正是在這個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陳獨秀成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隊伍的先驅者和擎旗人。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趙世炎、陳潭秋、何叔衡、俞秀鬆、向警予、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張聞天、羅亦農,等等,一大批先進分子在新思潮、新學說爭鳴斗勝的形勢中,經過反復比較、推求,殊途同歸,最終歷史性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到了這個時候,五四運動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當年,就有人對此情形作了這樣形象生動的描述:“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得風起雲涌了。報章雜志底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即布爾什維主義)﹔這裡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裡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仿佛有‘雄雞一唱天下曉’的情景。”
事實上,中國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和認識國家命運的工具來接受的。誠如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樣﹔“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他進一步分析道:“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