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如心與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建立
陳永升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它是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思想理論。大家都知道,劉少奇同志1946年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正式提出通過黨章把“毛澤東思想”正式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個說法的是蘇聯留學生、歸僑張如心。

張如心(1908-1976年),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08年,張如心出生於著名僑鄉——廣東梅州興寧。1921年,張如心進入廣東梅州樂育中學學習,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1925年因參加學生愛國運動被學校開除。同年夏到廣州學習,不久加入國民黨,轉至廣東國民政府航空局當宣傳員。1926年2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加國民黨留蘇學生黨部領導工作,是堅定的國民黨左派。1927年2月轉入莫斯科中山大學教員班學習兼做翻譯。1929年11月回國到上海,參與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籌備工作。
1930年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成立,張如心任研究部部長。1931年主持社會科學研究會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編著《哲學概論》一書,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對廣大知識青年學習哲學起到積極作用。
1931年8月,張如心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紅星》報主編、總政治部團政治委員訓練班主任。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他對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是“平凡而偉大”。
1934年張如心參加長征。到陝北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員。1937年8月起,任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政治教育科科長。后歷任軍政學院教育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黨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學副校長等職。
1938年9月,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基於中共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現實革命任務形勢的綜合考量,毛澤東在全會上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理論命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以具有民族特性的風格形式實現,抽象的馬克思主義無法發揮其變革社會的理論力量。目前中共面臨的亟需解決的重大任務,就是把帶有抽象性和原則性的馬列主義理論運用於帶有具體性和特殊性的中國革命實踐,在豐富生動的革命實踐中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他呼吁全黨從中國的革命實際出發去應用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表現帶有中國的特性。這一提法,極大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在全黨范圍內的順利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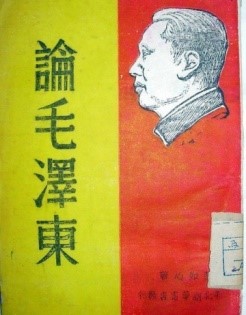
受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論述的影響,1941年3月,張如心在《共產黨人》第16期上發表了《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 一文,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概念,標志著黨內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予以較為系統的研究。文中指出,毛澤東基於對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發展規律的深邃認識,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上有了許多重要的“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底貢獻”,充分體現於他的著作和演講中。黨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忠實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該文首次將毛澤東視為“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張如心的理論主張很快得到黨內的熱烈響應。在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與會領導人高度評價毛澤東及其理論。同年底,中央“決定張如心調任毛澤東的讀書秘書”,表明張如心關於“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理論創見得到黨內決策層認可。
隨著中國共產黨改造黨內教條主義、倡導理論聯系實際的思想原則的整風運動展開,張如心繼續對毛澤東的思想進行研究。1942年2月,他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指出,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中國特殊社會形態中的創造性運用,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軍事路線這三部分有機的統一構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體系”。文中首次使用“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體系”這一概念,自覺地將其視為一種完整的體系,闡釋毛澤東思想的各個組成部分及相互關系,揭示其理論內涵及思想方法。為反駁國民黨文人葉青對“毛澤東主義”的攻擊,他在該文中首次從正面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指出毛澤東主義是指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是引領中國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的理論武器。該文是繼《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之后更為系統、深入地研究毛澤東理論和策略的文章。
1943年7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紀念建黨22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所有黨員干部應該用心研習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與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該文認可張如心“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提法,並將之視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不久,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確提出並多次使用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對其內涵第一次作了較為集中的概括和闡述。該文指出: “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引中國民族解放歷史進程的正確道路的理論總結。這一闡述所揭示的內涵,標志著“毛澤東思想”作為反映毛澤東著作本質特征的科學概念,經過兩年多的醞釀討論正式提出。文章還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理論原則與中國革命現實結合的產物,是吸取全黨的歷史經驗教訓、集中全黨智慧的成果。王稼祥提出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此后,“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逐漸被黨內外人士接受和使用,並在中共七大上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通過對“毛澤東思想”概念形成軌跡的梳理可以看出,張如心在黨內率先客觀、系統地評價毛澤東的理論貢獻,並對毛澤東的理論體系先后以“思想”、“理論和策略”、“主義”等概念命名。他的論述,揭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源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國發展的新階段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他對毛澤東思想予以體系化的總結闡述,意在確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黨內的指導地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理論創新進入自覺升華的階段。
此外,在對毛澤東思想命名的同時,張如心還將毛澤東的理論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殊國情下發展的產物,主張把毛澤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並列為革命導師。進而,張如心把毛澤東的著作賦予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中國的經典文獻並列的地位,視為運用馬克思主義揭示中國革命問題的經典文獻。毛澤東的著作應該作為教育黨員干部的課本。張如心認為理論工作者重視學習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古典著作是正確的,但是漠視以毛澤東的著作為代表的我們黨中央在許多中國問題上創造性的馬列主義文獻的現象必須糾正。張如心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一文中指出:學習黨特別是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創造性馬列主義成果,才能“成為中國的馬列主義者,中共布爾塞維克的干部”。學習毛澤東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如何把馬列主義理論原則、方法、精神貫徹到革命實踐中去,是順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部分黨員“漠視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這是我們黨目前公式主義傾向的主要標志之一,也就是黨性不純潔的具體表現”。應該說,張如心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因應了中國共產黨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趨勢,是中國共產黨改造黨內“言必稱馬列”的話語體系、形塑新的意識形態、樹立中國化思維導向的歷史進程的組成部分,它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全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另外,張如心通過對毛澤東同志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運用,批判了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張如心《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 一文,通過列舉分析毛澤東在中國問題上創造性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例証,從哲學層面詳細評述《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指出“從毛澤東同志編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徹地了解唯物辯証法的本質,如何把長期的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以辯証法的方法科學地綜合起來。……這與過去中國出版界關於辯証法的許多枯燥無味的公式主義的敘述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區別。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在辯証法唯物論上是有了許多新的發展,特別是在對立統一法則的具體應用上面”。1943年,張如心在《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在辯証法唯物論上的精深造詣,使得他能夠站在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思考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他在革命實踐中牢固把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最主要的就是“把理論與實踐的一致作為自己的基本出發點”。中國共產黨出現教條主義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對各種實際情況的了解不夠,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尤其是對毛澤東的著作重視不夠,甚至是漠視。黨要克服教條主義,必須學會馬列主義的方法。為此,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古典著作,而且還要細心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關於中國歷史與革命問題的諸多論著,學習他們具體分析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特點及其規律性的方法。張如心認為,馬克思主義最主要的特點和作風,就是堅持理論和實踐一致的思想方法。毛澤東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方法集中體現於一系列重要言論著作中。為了能夠更好地執行毛澤東的指示,黨員干部對於中國社會現狀要有全面深入的研究,發現特點,找出規律,這種研究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民族化的基石。
總結張如心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貢獻,主要表現為以下3點:
1.首先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理論概念,並將之理論體系化。
2.把毛澤東思想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特殊國情下發展的產物,把毛澤東同志的地位上升到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並列的革命導師,把毛澤東著作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黨內“言必稱馬列”的話語體系。
3.通過對毛澤東同志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運用,深化了中國共產黨黨內對唯物主義的認識,批判了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
(作者系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藏品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