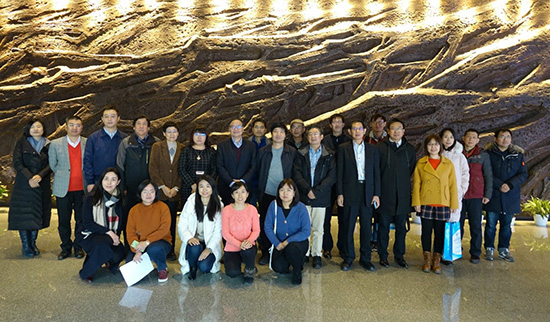2018年12月14日上午,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與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聯合舉辦“紀念《中日友好條約》締結40年暨中國改革開放40年日本華僑華人專題研討會”。在本次專題研討會上發言的專家學者有《日本僑報》出版社社長、日中交流研究所所長段躍中,日立(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留日博士蔡林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暨人文與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嘉庚講席教授劉宏,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呂耀東,日本桃山學院大學社會學系原教授過放,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龍登高,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奉林,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吉偉偉,天津理工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張慧婧。來自南洋理工大學、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等高校的研究人員、博茨瓦納—中國友好協會執行會長南庚戌以及僑研所全體同志參加了本次研討會。研討會由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副所長張秀明主持。


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所長張春旺首先代表會議主辦方致辭。他指出,中日兩國的交往源遠流長,兩國既是鄰國,又是地區和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大國,中日關系既對亞太秩序有重要影響,也對世界的和平穩定具有重大意義。古代徐福、鑒真等都為中日交流做出了貢獻,近代很多中國留學生赴日本學習先進的知識,再回國進行傳播,推動了中國近代的現代化和革命事業。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領導人都十分重視兩國關系,尤其是今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了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李克強總理出席了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招待會。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年,僑研所和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聯合舉辦此次專題研討會,旨在深度探討中日關系的發展及其對日本華僑華人的影響,日本華僑華人在中日友好關系中的作用,以及40年來日本華僑華人的發展變遷。

段躍中社長
段躍中社長作了題為“如何在日本講述中國故事——華人出版社的挑戰”的發言。段社長在近二十年的留日生涯中,一直致力於講述在日華僑華人的故事和中日友好的故事,期望培養了解中國的日本年輕人和了解日本的中國年輕人。1996年,他創辦《日本僑報》,用日語向日本主流社會講述中國故事,全面介紹在日中國人的情況。1998年,他出版《在日中國人大全》一書,收錄了1萬名優秀的在日中國人的材料,在日本社會引起很大反響。后來,他創辦全日本漢語作文比賽,迄今為止已舉辦了14年,一共有4萬多人參賽。2007年,段社長又開設“星期日漢語角”,11年來,舉辦了560多場交流會,來自10個國家的2萬多人參加。2008年,他創辦日中翻譯學院,10年來有300人參加該院的深造,30人獨立翻譯出版了中文優秀著作。段社長認為,應該發揮國際友人的積極作用,讓年輕人更多參與,共同講好中國故事。

蔡林海博士的發言題目是“中日經貿合作40年與在日華僑華人經理人的貢獻”。他首先界定了“華僑華人經理人”的定義,是指在國外跨國公司或大型金融機構,以經營管理工作為長期職業,具備一定專業素質和職業能力,並掌握企業經營管理決策權的華僑華人群體。他將在日華僑華人經理人的變遷分為四個階段:1970年代,日本公司開始開拓中國市場並在中國設立辦事處,那時負責中國業務的經理人主要是橫濱和長崎的華僑子弟﹔1980年代,在日本公司對華投資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戰爭孤兒的歸國子女﹔1990年代,經理人群體以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為主,他們畢業后被派駐中國。2000年以來,經理人群體又發生了變化,很多人都歸化日本,歸化華人成為日本對華經貿、投資、經營、管理的主力。2018年,早期留學生的后代也開始進入跨國公司,他們是日籍華人。蔡博士指出,中日經貿合作40年,經理人這個群體為中日經貿和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貢獻。

劉宏教授作了題為“比較視野下的日本與新加坡新移民群體及其同中國之關系”的發言,從比較的視野思考新加坡和日本的新移民社會。首先,數量上,隨著日本、新加坡和中國的關系正常化,中國新移民在兩國大量出現。其次,構成上,老一代移民來自福建、廣東等老僑鄉,而新移民既來自傳統僑鄉,也來自上海、北京、東北等地﹔新移民的專業技術人士比例很高,但也存在以勞工為主的現象,在結構上出現兩極分化。第三,社會組織上,新移民少部分以地緣為主,但已經跨越地緣界限,以中國為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對象。第四,與中國的關系上,兩國新移民都積極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中國的對外投資中佔有很大比重。劉教授認為,從華人社群的角度看,新移民在兩國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性﹔但從國家的層面看,差異性大於相似性。差異性主要體現在新加坡更關注如何把中國新移民融入當地社會,而日本的中國新移民受外交關系影響程度更大。

呂耀東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改革開放以來中日關系的歷史反思——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歷史承接性”。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日關系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平穩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的曲折發展階段和21世紀的反思與調整階段。改革開放40年來,中日關系從經濟層面而言互補性較強,但中日綜合國力的變化,使得兩國潛在的戰略沖突依然存在,同處東亞的中日之間的矛盾具有結構性特征。中日結構性矛盾通過政治、經濟和安全等方面表現出來。他指出,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未來仍是維護中日關系大局的政治基礎,應充分認識中日關系“不確定性”的長期性和復雜性,通過構建良性雙邊互動的渠道,不斷化解中日關系可能出現的困局。

過放教授作了題為“中日關系與旅日華僑——親歷者淺談”的發言。她從中日關系的特點與基礎、日本華僑社會的變遷、日本的華僑華人研究、日本的大學生與大學課堂及中日關系的發展趨勢與展望五個方面展開。40年來,旅日華僑的人數從約5萬人增至70多萬人,並有1000多萬中國游客赴日旅游。中日關系對旅日華僑的影響,與其他國家相比更為強烈。中日關系從“友好、對立”走向“協作共贏”,要推動中日關系進一步發展,其中的關鍵是開放、學習和擔當。

龍登高教授作了題為“‘世代華僑’的身份與權益——傳統華僑的遺存及其新問題”的發言。“世代華僑”是指世代出生和居住在外國,至今已是第二、三甚至四代但仍然保留中國身份的華僑群體,以韓國、日本華僑為代表,與此相似的還有一些未加入外國國籍的海外人才。他們在中國國內已經幾乎沒有任何權益,但在居住國又沒有國民待遇。因其身份和証件特殊,在現有政策下遇到多種困難,特別是回國留學、投資、就業甚至旅行等方面。有一些高級人才長期在海外工作,仍持中國護照,但沒有中國國內戶口和身份証,國內的待遇、福利與權益都與之無緣。僅憑國籍來區隔華僑與華人的相關政策,將此類特殊華僑排斥在外,他們在國內的各種權益和待遇應該引起學界和有關部門的關注與研究。

陳奉林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對中日民間交流多種影響因素的思考”。中日之間的民間交往悠久歷史,徐福、大禹等中國歷史和傳說中的人物在日本有很高的知名度,這些都是中日民間交流的很好印証。近代去往日本的中國人非常多,學習日本的各種知識,回國辦學。陳教授以自己求學和訪學的親身經歷說明,民間輿論不斷影響中日之間的交往。他認為,在中日關系的發展過程中,民間的力量非常大,一直在推動著中日關系向前發展。現今,在中美關系面臨挑戰的時候,或許是中日關系推進的一個契機。

吉偉偉副教授的發言題目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赴日留學移民的變化”。截至2018年10月,日本在留外國人達263萬多人,佔日本總人口的2.1%,其中中國人約有74萬,以20至34歲的留學生群體為主,約佔在日中國人總數的56%。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留學理念發生了變化,1948年—1979年,留學主要是國家“公派”,改革開放之初的留學潮是中國根據優先和需要學習先進科學技術這一理念開啟和驅動的,隨著20世紀90年代留學產業化意識的增強和個人意識取向逐漸受尊重,中國一直限制的自費留學慢慢成為留學的主流。留學移民發源地也發生了變化,20世紀80年代,北京、上海和福建是改革開放后首批留學移民發源地,20世紀80年代中期,自費留學開放后,日本語言學校的簽証手續變得相對容易,中國留學生的來源地日益多元化。他指出,中國赴日留學移民的動機、渠道等都發生了變化,當代日本留學移民從“日本盲信”進入了理性再思考的階段。

張慧婧副教授作了題為“日本外國人政策的變化及其對中國新移民的影響”的發言。她指出,日本政府一方面大量引進外籍勞動者,另一方面卻又拒絕承認其“移民身份”,至今未開放移民政策或出台系統規范的《移民法》,體現出在勞動力填補與移民問題上的矛盾心態。她認為,日本作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少子老齡化國家,加速引進更多外援、填補勞動力缺口是當務之急。日本已經在事實上成了新的移民國家,卻在表面上拒絕承認移民。沒有全方位的移民政策作為支撐,必然影響外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和生活福祉,造成社會矛盾和摩擦增多,甚至導致被迫犯罪行為,令原本就意識保守的日本民眾更難以消化日本政府猛然提速吸納外國人的舉措。對外國人政策的基本方針止步不前正是引發社會問題的關鍵症結所在, 亟待從根本上解決。

張秀明副所長在總結時指出,本次會議是近年來中國華僑華人研究領域舉辦的首次日本華僑華人的專題研討會,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既有在日本留學、工作的親身經歷,又有長期關注中日關系、日本華僑華人的研究積累,從不同角度對中日關系及其對日本華僑華人的影響、日本華僑華人的發展變遷、日本華僑華人在中日關系中的作用,提出了富有見地的看法,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此次會議搭建了國內外學者深度交流的平台,希望今后大家能進一步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推動日本華僑華人研究取得更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