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蔣宏達、徐世博
本文轉載自《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蔡志祥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很廣,包括華人社會的節日與民間宗教、近代中國的家庭與宗族、中國商業史、華南及東南亞華人社會。在他個人網頁上有一段學術自述,很能反映他的學術旨趣。他說:
“我有興趣的歷史是當代的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政府如何談論、解析和運用過去來建構現在。也就是說,我有興趣的是歷史如何在不同的時代、被不同的群體敘述和再述﹔在重整歷史的過程中,過去如何被選擇和遺忘、想象如何被歷史化、事實如何被妝飾化﹔誰主宰對過去的討論,沒有聲音的個人和群體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可以從哪裡知道。也許,我嘗試追求的歷史,是在思考和學習過程中不斷地模塑的自我。”
在訪者的印象中,蔡先生朴實而睿智,對很多研究議題都有獨到見解。以至在很多學人講座和會議的場合,如果他在場,聽眾們每每會期待聽到他的提問或點評。他的發言常有各種巧思,給人很多啟發。
在約訪時,訪者曾經寫道,可以把主題設在華南研究的跨地域聯系的視角上,因為包括訪者自己在內不少從事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年輕學生往往“困”於個案之中,因不知如何走出一些既有框架的限制而倍感迷茫。同時,訪者也希望,通過他的講述可以展示一點華南研究中尚不大為人熟悉的地方。

東方歷史評論:蔡老師,您好。我曾修讀過您的不少課程,特別是其中“中國的商業與社會”、“近代中國的節日和民間宗教”和“僑鄉研究”三門課,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們發現,這三門課大致對應著您的三個主要研究方向:商業史、節日與宗教、華南-東南亞華人社會。您能不能結合自己的治學經歷來談一談您是如何進入這三個方向的研究的?
蔡志祥:好的。我最初主要做經濟史研究,碩士階段研究的是近代湖南的米糧市場,那時沒有想過要研究節日和宗教,更沒有想到要研究海外華人,對后來興起的“歷史人類學”也沒有多少概念。一開始我的興趣集中在“經濟”和“政治”上,對“社會”產生興趣,應該說是受了人類學的影響。我在中文大學讀書時,擔任過人類學系的助教,結識了華德英(Barbara Ward)教授,是她建議我關注鄉村社會。那時,我意識到,如果要了解中國社會,就必須了解家庭和宗族。這一點也是從人類學那裡學來的,因為人類學最基本的就是研究人跟人的關系。要搞清楚這些關系,首先就要研究家庭。我在閱讀湖南的史料時,注意到了家庭和宗族的作用。后來去日本留學,東京大學那邊收藏了不少族譜,於是我開始研究族譜。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幾個很重要的理論,一個是弗裡德曼的宗族理論,一個是施堅雅的市場結構理論,另外還有華德英、武雅士(Arthur P. Wolf)的理論。我研究湖南經濟的時候,關注的是施堅雅的理論,做博士研究時又注意到了弗裡德曼的理論。不過,當時華德英跟武雅士的東西還沒有進到我的頭腦裡。
我對商業史和海外華僑的研究是博士畢業回香港后開始的。那時我在香港檔案處工作。一天,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先生許舒(James Hase)博士來檔案處找我,告訴我他收集了很多地方文獻,其中有一批契約,問我有沒有興趣替他編輯。當時,我覺得自己應該可以勝任。因為在日本讀書時,我曾參加過一個土地文書研究會,每月和東京大學的一群學者,包括佐伯有一、岸本美緒等,聚在一起研讀契約,所以對契約還是比較熟悉的。我在檔案處待的時間不長,大概一年半后就去了澳門。在澳門,我開始整理這批契約。
這些契約有兩百多件,都來自一個潮州人家庭,他們在香港經營“乾泰隆”商號,“乾泰隆”曾是全港最大的南北貨商號,所以我對這些契約很有興趣。不過,那時我完全不了解潮州,既沒去過潮州,也沒看過跟潮州有關的研究。當時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些人是什麼人,他們去過什麼地方?要回答這個問題,我需要跑到他們的家鄉潮州去,看看這個家庭在當地是什麼樣的。另外,考慮到乾泰隆是一個家族企業,有一百多年歷史,從汕頭、香港,到曼谷、新加坡都有他們的生意,所以又想跑到海外看看情況怎樣。我就從這裡開始了新的研究,有機會將地方宗教、節日與海外華人社會聯系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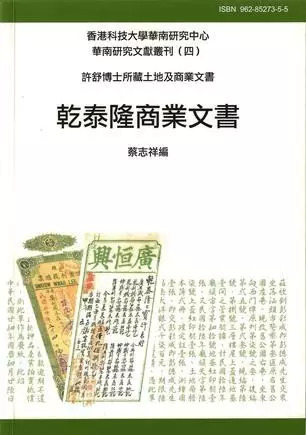
我初次去潮州做田野是在1990年,碰巧遇到了那裡的游神活動。當時,我對宗教儀式並不是很懂,只是希望通過儀式了解當地的社會結構是怎樣的?人們怎樣通過文化活動同海外產生聯系?我漸漸明白,這裡涉及到商業與文化的關系,需要從文化資源的角度來理解商業的發展,把商業放回到跟家庭、宗族關系中去。就是這樣,一開始是做一些雜雜的研究,慢慢地就將很多東西匯聚、貫通起來。
東方歷史評論:近代以來,很多源自中國本土的節日和民間宗教活動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得到了延續,成為一種“全球現象”。您如何看待這些活動在聯系海外華人社會和中國原鄉中的作用?
蔡志祥:說到海外華人與中國原鄉的關系,我們需要注意的是時間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同時間離鄉的人,跟家鄉的聯系是不一樣的。如果你剛剛出洋,你的父母家人可能還在那裡,跟家鄉的聯系就是一個家庭的關系。假如已經隔了幾代,你在家鄉可能一個人都不認識了,就不存在現實的聯系。
有個定居在新加坡的潮州人去世前曾同我談過他小時候在鄉下的各種生活經歷。但是當我同他兒子交談的時候,就完全沒有這種經驗。他的兒子是一個很有名的畫家,他也很喜歡家鄉潮州,但是他喜歡的那個家鄉跟他父親的家鄉並不一樣,那是一個藝術家眼裡的家鄉,而不是真正生活過的家鄉。假如隔了幾代之后,海外華人還要為家鄉做一些事情的話,就要從“家庭關系”轉到所謂的“宗族關系”。對於家庭,我們可能有一種直接的義務,規定了我們需要做什麼。但對於宗族,那就是一個可以選擇的,而不是義務的東西。
另外,我從乾泰隆的例子發現,有時候海外華人在中國原鄉做的事情,可能也不見得一定跟家鄉有關。大概在1994、95年的時候,乾泰隆在曼谷的那個家族給潮州當地捐助了80萬港幣,地方干部都很高興,稱贊他們愛國愛鄉。事實上,他們的這個行動更多地是出於維持自身在曼谷的僑領地位的考慮。
節日這類事物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在於它能把外面的人吸引過來,但是這種吸引力究竟有多大的功效,我也不清楚。從1980年代開始,有很多新加坡人回中國內地建廟,重新建立起與原鄉的聯系。我在新加坡九鯉洞調查時了解到,當地的儀式專家與福建莆田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莆田儀式傳統經歷過斷裂,當地在80年代恢復儀式活動時,要從新加坡華人社區引進。到了21世紀,新加坡又反過來要從莆田引入儀式專家。當他們在重建聯系的時候,不光有“出口轉內銷”,而且有“內銷轉出口”,就這樣倒來倒去。
東方歷史評論:您的這些看法讓我想到此前您在AoE(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工作坊裡做的報告。您提到了傳統的忘記、消失和再現,也提到“行動”在節日和宗教活動中的重要性,指出“節日”是“行動中的社會”。
蔡志祥:這個問題是在回香港的飛機上突然想到的,開會前一天晚上才慢慢整理出來。我覺得,我們常常把文化傳統當作一個理所當然、前后連貫的東西。但是,傳統很多時候,就像蕭鳳霞教授在那篇有關小欖菊花會的研究中揭示的那樣,是一個“循環再生”的過程。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一個傳統、一種文化很有歷史,但實際情況往往並不是這樣。很多傳統被中斷了,很多文化被廢棄了。對傳統而言,“忘記”是一種常態。忘記一種傳統並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你隻要停止了,不做了,自然就會忘記。但是,某一天,當你要把已經中斷的傳統重新恢復起來的時候,就需要採取一些特定的行動。我的想法是,忘記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再記憶卻是一個刻意行動的過程。正是在“再記憶”的過程中,“行動”的意義凸顯了出來。我想你們讀過很多地方志,地方志裡有很多關於地方廟宇、廟會的記錄,也有不少宗教制度的記載,但是這些宗教活動和宗教制度不是理所當然地一直保存下來的,它要維持下來就必須依靠人們的行動。這些讓人恢復記憶的行動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重點。我想強調的正是“再記憶”過程中“行動”的重要性。
東方歷史評論:您在研究東南亞華人社會時,提出要理解中國性(Chineseness)的問題,在您個人看來,所謂“中國性”指的是什麼?
蔡志祥:我想,當你身處海外的時候,可能面對兩種處境。一種是你在當地活不下去,返回故鄉。另一種是你留在了當地。留下來也有兩個方法:一個就是把你自己變成當地人,另一個就是讓當地人感覺到你這一群人的重要性,不能把你們清理掉。在海外的華人社會中,有很多人會跑回來,也有很多人變成當地人,但是更多的人還是用了他們自己所認為的傳統維護自己的中國認同。比如說,我是中國人,所以過年就要舞獅子,清明節就要去拜山祭祖。在研究海外華人社會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就能發現很有中國色彩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是否源自中國本土其實並不重要。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很多所謂的中國節日和儀式在中國基本上都不做了,或者做法很不同。比如,幾年前,我們去馬來西亞新山考察游神活動,發現那裡的儀式實際上是柔佛當地華人自己做出來的東西。又比如新加坡現在有一個規模很大的九皇誕,我們當然可以在中國本土的道教儀式中找到九皇誕,但是東南亞華人的做法與中國道教裡的很不一樣。他們在裡面添加了很多本土的東西,比如神童上身,這在正統道教儀式裡是不可能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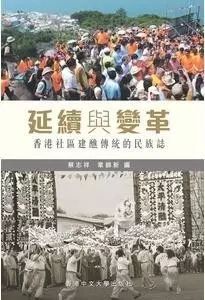
海外華人很重視這些節日,他們覺得這才是中國傳統的節日,是華人的節日,但實際上有很強的地方氣息在裡面。他們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些節日和儀式,讓自己成為一個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重要的少數群體。假如沒有這些節日和儀式,馬來西亞政府、泰國政府可能就會覺得,華人都同化了,不需要為關照華人而制定特定政策。如果我們想要讓政府覺得在馬來人、印度人之外,還是有一個“中國人”(華人)群體的存在,就需要節日和儀式。我想,這種想象的“中國性”最重要的不是真的回到中國,甚至也不是要跟中國挂鉤。在地方社會,人們並不一定需要這些東西,但他們要在那個地方生活,就要建立一個“我”跟“你”不一樣的東西,強調我們的世界總是存在一些距離。他們對這些所謂“中國性”的強調,主要不是為了加強與祖國的聯系,而是為了讓自己在“中國”以外,在沒有“中國”的地方生活得更好。
東方歷史評論:2015年6月份,您組織過一場題為“跨國危機的應對:1850—1950東亞港口城市華人的社會經濟生活”的國際會議,由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共同探討近代歷次跨國危機之下,東亞華人的社會經濟、身份和文化被跨域的商品、人脈、知識和信息往來所影響和型塑的過程。我們想了解一些您當時對這個會的構想,為什麼以跨國危機作為一個主要的切入點?
蔡志祥:談到跨國危機,我最初的想法是從商業史中的“商品鏈”概念開始的。所謂“商品鏈”就是指商品從一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它具有流動性。這是我討論跨國危機的起點。過去我們談到商品鏈,談的主要都是商業、商品鏈,物流群組的實質內容。假如我們跳出商業的范疇,我們會看到在生活中有很多東西,都可以用這些商業概念去理解。例如,在研究流動性時,港口城市是很重要的研究對象,我們要研究港口城市的流動性不單要研究港口城市的商品,也可以從人流、知識和資訊流通的角度加以考察。
那個會的一個想法就是危機。我認為,在1850年代到1950年代這一個世紀之間,在東亞港口-城市生活的華人見証了最少三個沖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認同的跨國危機:一是1880 年代到1920 年代之間的鼠疫和港口衛生的問題。人口的流動讓瘟疫和疾病普遍傳播,目前學界有關疾病史、瘟疫史的研究很多。這些研究有的會從制度的角度講怎麼樣解決瘟疫、鼠疫的問題,有的也會借由瘟疫、疾病來講每個港口都發生了什麼事。我的問題是:鼠疫跟著人在港口流動,我們應當怎樣去理解這種流動?二是1920 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也就是所謂的“大蕭條”。三是1940至1945年太平洋戰爭,日本佔領中國南方和東南亞地區三、四年間,政治軍事帶來的地方沖擊。我有興趣的問題並不是疾病、商業或戰爭本身,而是思考人們在面對這些危機的時候,怎樣調整自己的生活。
在這些危機中,人是怎麼樣生活的呢?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密封的世界,你有很多的知識需要同別人分享交流。即使是舉行儀式的人,為了解決這些危機,也需要互動。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生活。我有興趣的是生活的問題。例如,你看東南亞的一些大型的儀式,他們請的道士也是需要進行分享交流的。2004年,我在檳城看到的儀式中不光有來自馬來西亞本地的道士,還有香港的道士。而新加坡的一個祭幽法會上,他們就不請新加坡本地的道士,而是請香港的道士。即便是在區域性的節慶儀式裡也有跨界的交流與互動。那麼,我想問的是,在危機的情況下,這種流動又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呢?19世紀下半葉開始,新聞報紙的出現讓資訊流動起來,而信息的流動又如何影響到當地的人對這些危機的應對呢?我覺得,我們看危機不能隻看一個地方,一定要帶有跨域的視角。

東方歷史評論:您有很多有關跨地域聯系的思考,針對目前很多年輕學者將特定區域的歷史作為研究選題的現象,您認為他們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蔡志祥:對年輕學者而言,大膽嘗試非常重要。這幾年我看到很多論文題目,發現大家很多都傾向於做個案研究,這些選題看上去都很“安全”,但問題在於你要嘗試著走出來。我想,如果要從個案中走出來的話,你就不能單純從一個很physical(現實)的地理去看,而是需要在一個想象的空間裡把你想做的東西串聯起來。
談到地域社會,我們基本談的都是宗族,有時候也談廟宇。當你談宗族、廟宇的時候,你要注意到宗族本身是流動的,廟宇也可能存在分支。一旦確定這些制度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我們就需要注意不同宗族和廟宇之間的界限。這種界限有時是很模糊的,有時出現在人的生活想象中。這一點我在觀察香港的打醮儀式時有很深的感受。在儀式的過程中,他們最后都會把“臟”的東西丟掉,但他們既不能夠把“臟”的東西丟到自己的村子裡,又不能夠丟到隔壁村子去。事實上,村子裡的人都知道哪裡可以丟,哪裡不能丟。界限這種東西,並不是真的能夠清楚劃定的,即使很清楚地劃定了也會出現很多爭議。那麼,當出現爭議的時候,我們究竟要如何跨越想象的界限去理解這些課題呢?我認為,要把諸如誰的話語權大、誰的政治權力大這樣的因素考慮在內。地域制度層面的一些東西,是可以把我們的研究聯系在一起、實現跨區域比較的。
此外,我還需要強調一點,就是在區域研究中,我們到底能不能夠找出一些通則或者“模式”?盡管我們不能用單一的理論去解釋所有的東西,但是我們需要嘗試把理論放到不同地方社會的具體情境中去理解。這樣,一些研究結論就不單只是在比如浙江的村子裡可以得到展現,而是可以應用到比如湖南或其他地方去。反過來也是一樣。
東方歷史評論:近年來,您和您的團隊在湖南沿洞庭湖周邊進行研究,據我所知,這個團隊的學者來自各個領域,研究的區域也各不相同,您能不能談一談對這個研究項目的理解?
蔡志祥:首先我得說去湖南調研是被迫的,不是自願的(笑)。當然,團隊成員黃永豪、呂永昇、謝曉輝、陳瑤等人都有自己關注的區域,不過我們很早就覺得有必要嘗試做一些跨區域的研究。我們一開始想從“祖先”的角度去觀察區域歷史。比如陳瑤從湘江那邊看“祖先”在當地是怎麼樣做出來的,呂永昇在湘中研究這個問題,謝曉輝則在湘西。那時候,我們希望通過一個制度或標簽,理清同樣的祖先信仰在不同地方的演變歷程。當我們將研究成果編輯成書的時候,又想嘗試對台灣、湖南跟西南地方的儀式進行比較。我們初步的看法是將洞庭湖看作一個“磁場”,在地理上把眾多的商業、人群吸引過去。其實,這種“磁場”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不只是洞庭湖,在通商口岸也一樣。我們想利用“物流群組”這樣的一些視角,用“磁場”的概念去看跨區域的聯系。
東方歷史評論:那天聊天時,您提到下一步要回歸商業史研究。您從經濟史、商業史出發進入社會史研究,現在又回到商業史研究上去。您有怎樣的考慮?
蔡志祥:我為什麼會回到商業史的研究?簡單地說,過去十多二十年裡,商業史的研究方向和理論,對我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幫助很大。很多關於民間宗教、儀式行為的構想,都始源於商業史中組織的層階架構、網絡和跨域市場關系、博弈和決策選擇等知識。我覺得是時候從家庭宗族結構的研究、從民間宗教的研究,以及從跨域的研究,反饋商業史。
商業史的研究中關於非物質資源的觀點無疑與宗教節日的研究很接近。但是很多研究宗教的朋友,其實很反對對宗教活動背后一些隱藏的利益考慮。我記得,和很多朋友談到台灣早期的王船信仰和鹽走私的關系的可能性時,研究宗教的朋友很快的反應就是王爺這麼凶,誰敢利用他來走私。同樣的,我寫關於汕頭善堂的出現和苦力貿易關系的文章時,也碰到不少不同意的聲音。當然,這都要回到文獻資料的証據。
在關於乾泰隆的研究中,我斷斷續續的寫過親屬關系和商業機構內部結構和繼承關系的文章,也寫過文化交游網絡、家鄉建設等和商業發展關系的文章。有關契據結構的文章其實是從宗教節日參與的權利和責任,或和神明的契約關系中發想而來的。人類學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明白社會。我從1990年開始碰觸商業史的問題。九十年代后期以來,大部分時間放在宗教節日的研究。我相信是時候嘗試把兩者整合,希望可以對商業史研究稍有貢獻。我認為做研究的人要有膽量挑戰自己熟識的框架,要有想象力把不可能的東西嘗試鏈接起來,要跳出時間和空間。當然,最重要的是我們怎樣串聯和解釋手中的材料和証據。這樣的話,也許對商業、節日、民間宗教、華僑華人、家庭和宗族的研究會出現一些新的天地。







